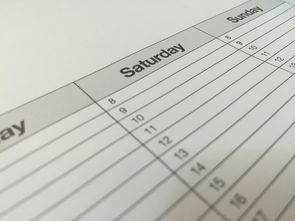论犯罪与刑罚电子版(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2000字)
最近读了徐九生先生翻译的李斯特的《论犯罪、刑罚与刑事政策》,并与我记忆中的《论犯罪与刑罚》进行了比较。另外,我之前读过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对刑法体系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不禁思考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具体的操作方法。比较两个经典刑法流派,无论从犯罪论还是刑罚论的角度来看,李斯特的刑法理论当然比贝卡利亚的刑法理论多了一层刑事政策。事实上,刑法的研究离不开犯罪理论、刑罚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衍生。
首先,任何刑法学派都不可避免地必须提供符合其自身体系的犯罪解释,正如哲学家必须回答物质与知识的优先性一样。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困难之一是定义相关社会现象的概念。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古典刑法学派对犯罪的定义稍显简单。它认为犯罪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行为。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犯罪是利益与犯罪所得的比较。当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因犯罪而受到的惩罚而损失的利益时,就会发生犯罪行为。然而,个人意志的确定加上功利主义提出的人是理性人的推定,无疑将犯罪概念的范围限制在故意犯罪的范围内,而忽视了过失犯罪的存在。此外,犯罪的定义也无法解释饥饿的无家可归者偷面包的问题。为什么无家可归的人要冒着遭受痛苦惩罚的风险去偷面包,而这会导致他失去自由?自由和面包之间存在着鸿沟。利益对比显然是毫无疑问的。自由从古至今一直是最重要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多年来,许多人为了个人自由而牺牲了生命。因此,未来不同的刑事律师提出了更多不同的犯罪定义。比较著名的是龙勃罗梭提出的“天生犯罪论”,认为犯罪是从出生就决定的,总结了犯罪分子的定义。人们甚至相信犯罪可以通过基因遗传。但菲利对犯罪人类学有些怀疑,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学派的成员。他把社会因素纳入到犯罪因素的考虑之中,并与人类学因素和物理因素并列。不过,李斯特仍然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物理因素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因此他将人类学因素和物理因素融入到个人因素中,将费城的三个犯罪因素转化为两个犯罪因素。同时,将这两个因素划分为优先级。研究犯罪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因素,但社会因素稍微重要一些,因为它涉及到相应刑罚措施的实施和刑事政策的制定。“我一直用的说法是:犯罪一方面是犯罪人实施犯罪时人格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外部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李斯特还认为,人类的犯罪史与人类的社会史总体上是一致的,所以对于犯罪,首先要分析其形成的社会原因,然后再分析作为社会细胞的人。
如果说讨论什么是犯罪是对犯罪的形式回答,那么讨论什么是犯罪标准则是对犯罪的实质性回答。同样,李斯特也坚持以侵犯法益理论作为犯罪的标准。他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批评了宾丁在其著作《刑法手册》中的概念,认为他没有区分抽象与具体、概念与客体,并将其称为法益概念。它只是一个虚幻而空洞的词,因为它的内涵没有一个稳定的范围。它有时与事物混淆,有时与重大权利混淆,从而造成Binding自身刑法体系的混乱,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上,还是体现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李斯特认为,刑法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需要运用法学的方法论来构建自己的科学体系。法学的方法是不断收集规范材料,分析这些规范中相关的主谓概念,通过上位概念和从位概念的提炼,形成有序的体系。李斯特认为,法律利益作为一个一般抽象概念,不应与刑法具体法律条文的具体概念相混淆,而应从这些具体概念的共同点中抽象出来。法益作为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需要从较高层次的概念中抽象出来。它可以源自低层概念,因此在李斯特看来,合法利益与当今刑法的一般客体类似。他认为,“合法利益的概念是抽象法律逻辑的有限概念……我们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称为合法利益。”
其次,事实上,民法与刑法的界限并不明确和明确。“有权利就有救济”这句话也可以适用于刑法,但需要稍微转化为“有罪就有惩罚”。惩罚是作为对犯罪的补救措施而存在的。毫无疑问,刑罚的合法性在于它来自人民的授权,通过社会契约,以国家暴力为手段来惩罚侵犯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从古典刑法学派的角度来看,惩罚是一种以己之道报应人的报应性惩罚。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惩罚是减少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所能获得的利益,同时增加犯罪所受到的惩罚的痛苦。虽然这样的惩罚解释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在实践中却会产生相反的反应,增加酷刑的发生。不能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古典刑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一情况。他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他认为,刑罚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其残酷,因为无论刑罚多么残酷,都会使罪犯死亡。因此,残酷的惩罚甚至可能会变相促进残酷犯罪的发生,因此他提出,惩罚的有效性取决于执行的及时性。但这种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及时性并不能完全取代残酷性,因为报应目的的存在。李斯特改变了想法。他认为惩罚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以本能行为的形式存在,类似于洛克的自然状态。由于每一个自然人都拥有判断的权利,李斯特认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有惩罚的权利,都可以对违法行为做出本能的惩罚。然而,这种状态并不是静态的。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类的本能行为会慢慢转向有目的的行为,本能的惩罚也不例外,也会转化为有目的的惩罚。那么惩罚的权力就从带有报应思想和偏见的人手中转移到公正、中立的国家机关或社会机构,从而使对本能行为的惩罚得以客观化。“刑罚客观化的结果是刑罚适用的前提被确定。”条件还决定了以惩罚形式反应的内容和范围,使惩罚服从于目的理念。”然后根据行为人侵害合法利益的行为程度做出适当的惩罚,从而能够有效、从根本上避免残酷的惩罚。如前所述,对本能行为的惩罚转化为对有目的行为的惩罚,惩罚从属于目的的理念,这是刑事法学学者探索的必然。惩罚的目的。在古典刑事律师的思维中,惩罚的目的仍然是报应、及时报应。李斯特认为,惩罚的目的是威慑和矫正。威慑是一般的预防目的,威慑犯罪者和潜在犯罪者矫正是一种特殊的预防目的,对犯罪者进行矫正,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避免再次犯罪。由于古典刑法学派在现代刑法学派兴起之前占据主导地位,李斯特时代充满了报应性短期监禁。根据犯罪统计,这种短期监禁并没有有效降低犯罪率。相反,犯罪率却上升了。李斯特认为,这是滥用短期迁徙自由的后果。短期自由刑期可以是几天到几周,但不超过两三个月。一是刑期过短,不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第二,缺乏单独监禁,监狱将成为犯罪学校和犯罪人才的摇篮。因此,李斯特认为,应将犯罪者分为三类(不可纠正者、需要纠正者和偶尔犯者)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不能矫正的,处无期徒刑、劳教;需要矫正的,处相应的自由刑,释放后管制;屡犯的,处以罚金;如果他们无力支付罚款。处决应以不加监禁的惩罚性劳动取代。这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处罚体系。
最后,李斯特认为,在了解了犯罪的原因和惩罚的效果之后,我们还必须相应地打击犯罪,引入犯罪生物学和犯罪社会学,并制定经过验证的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科学的基础。刑法的一个分支,与以前对犯罪和刑罚的法律研究相结合,形成所谓的刑法整体科学。“所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借助刑罚和相关机构,在对犯罪原因和刑罚效果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用于打击犯罪的一整套原则(总称)。”。这与古典刑法学派只注重刑法概念研究的区别。犯罪生物学具体包括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精神病学。通过犯罪心理学,我们可以区分出上述不可矫正的犯人、需要矫正的犯人和偶犯。通过犯罪精神病学,我们可以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犯罪行为。即使他们不一定负有刑事责任;犯罪社会学主要是犯罪统计,通过各类犯罪的发生情况来分析犯罪现象发生的社会条件,为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李斯特对短期监禁刑罚的改革是基于犯罪统计数据提供的短期囚犯的累犯比例。除司法改革外,短期徒刑改革——引入了附条件量刑制度(类似于缓刑制度),刑罚改革——增加了短期徒刑的最低刑期,设想无限期徒刑(仅规定最低刑期和最低刑期)。最长期限),并寻找短期监禁。自由刑的替代措施(罚款、禁止外出、非刑事担保等)还包括制定刑事政策。李斯特提议设立刑罚执行监督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法官、检察官、监狱长等,他们在法庭以及监狱和其他刑罚执行机构中保持中立,他们对被判处自由的罪犯进行监督,并有权在执行无限期徒刑期间(至少在最低年限之后)释放或延长监禁期限,从而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减轻了刑法设定刑期的负担,也可以监督罪犯得到纠正的程度。相关刑事政策还包括对轻微犯罪的强制教育措施。虽然轻微犯罪也包括故意犯罪,但大多数是意外犯罪。因此,李斯特认为,不应判处未成年人自由,以避免其他犯罪。受狱中其他罪犯的影响,他们变得更加暴力。同时,李斯特还认为,有条件量刑制度(缓刑制度)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再加上义务教育措施,未成年人将获得两次被刑法宽恕的机会,有违法律原则和合理性。义务教育制度包括家庭教育和惩教教育两种类型。两种方法不能绝对相互转换。同时,也取消了对未成年犯识别能力的确认,因为未成年人的认识仅限于表面,未必能够理解法律制定背后的原理。它不能被视为与成年人的认知能力相同,因此应该通过教育系统培养他们判断道德价值观的能力。最后,李斯特还认为,义务教育制度应该扩大到适用于无人监管的儿童,即使他们没有犯罪,以防止他们在社会中徘徊、误入歧途。可见李斯特的刑事政策和刑罚有很大的不同。刑事政策有时可以影响刑罚的制定,有时也可以影响刑事司法的决定。更多时候,刑法是通过犯罪生物学和犯罪社会学发现的。存在的问题,通过政策加以解决。
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
版权声明:本文由浙江合飞律师事务所结合法律法规原创并发布,除法院案例栏目内容为公开转载,如无特殊声明均为原创,如需转载请附上来源链接。